|
老域名 http://www.china-langsha.com/ 《大国小民》第1219期 本文系网易“大国小民”栏目出品。联系方式:thelivings@vip.163.com 1 2020年底,新塘街道发布了一连串“拆违”公告,我家老宅所在的“文明巷”也是重点“拆违”的片区之一。 文明巷总长不过百来米,两边都是千禧年后新建的七层落地房,刚好将一片老房子夹在正中间。因为缺乏管理,巷子里到处都是居民扩建的墙根、简易棚,过道十分狭窄,算上排水沟也过不了两辆车,最窄的地方甚至挤不进一个胖子。街坊都说,文明巷是全街道最冷僻的角落,谁都想不到这儿居然还住着几户人家。 早在前几年,新塘街道辖区就被上级纳入城镇土地规划,附近商品房的价格已经超过2万,可谓寸土寸金。辖区内的那些未经改造的败落老片区,一下子就成了敏感话题。 朋友小深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,他在微信上告诉我,这个“百日攻坚”的“拆违”计划酝酿已久,如今疫情态势逐渐平稳,街道办就将它重新提上了日程。 “怎么,终于要拆自家的房子了?”我发了个坏笑的表情。小深也曾是文明巷的住户,父母留给他的那栋二层小楼,这些年一直租给外省务工人员住,他已经搬出去十多年了。 小深很快回复:“那倒不至于,现在要拆的是‘三类房’。” 新塘辖区的违建分为三类:第一类是90年代之前的违章建筑,属于土地确权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,既不会被强行拆除,将来征收时也会得到补偿;第二类是90年代兴建的违章建筑,属于可拆可不拆的变量;第三类,则是近些年偷偷新盖的。 过了一会儿,小深发来一张图片,是即将要贴出去的通告书:“你瞧,街道先定了两个目标,巷头和巷尾。” 我看了一眼通告书,眼皮不觉地跳动了一下,向他再三确认:“你们要拆老金家的棚子?” 小深说“是”,我的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。 住在文明巷巷尾的老金,是个先天性智力落后者。 他出生于50年代,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同。同龄的孩子长到三四岁已经可以蹦蹦跳跳到处疯跑了,他却刚刚学会站立,喉咙里还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。再大几岁,别的孩子可以干点农活了,老金连家门都没迈出过几趟,仍跟着母亲金婆婆“咿呀咿呀”地学说话。 他的父亲金大爷当过生产队的会计,人很精明,把家里的日子过得很兴旺。在有了老金之后,他和妻子又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,都很健康。老金虽是长子,却是被弟妹们带大的。 因为有家里人的帮持,老金的生活倒也舒坦,身上干干净净,无需工作,终日在街上晃悠,饿了就吃,困了便睡,无忧无虑。就这样年复一年,眨眼老金就30多岁了,他皮肤白净,个子高,头发带点自来卷,眉目里有些少数民族的味道,心性却还像个没长大的孩子。 金大爷本来没打算给大儿子娶亲,毕竟智力落后者不是普通病人,一傻就是一辈子,哪敢祸害人家姑娘。可是,他们终究耐不住别人说和——当时,邻村有个叫阿玲的女孩,也是先天性智力落后,和老金年纪相当。阿玲家里很困难,父母种了几亩田勉强维持温饱,实在没有余钱养她一辈子——如果成了家,她也许能给老金留下点血脉。 于是,老金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。阿玲(后来我们这些孩子都叫她玲婶)长得不太好看,身材矮小,头发枯黄,与高大的老金很不般配。老金哪懂“结婚”是什么,只是在父母的安排下,和同龄人一样有了妻子,有了家庭。 婚后不久,老金的儿子小金呱呱坠地。有时,夫妻俩带着小金在家门口玩耍,玩腻了转身回家,独留下小金一个娃娃。幸好金婆婆身体不错,一边照顾孩童般的儿子媳妇,一边亲手教养孙子,还能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。 那些年,老金的日子过得不坏。 2 随着小金慢慢长大,他智商发育迟缓的问题也渐渐显露出来。上了小学后,小金愈发呆板孤僻,连最基本的加减乘除都弄不懂。这似乎是一场早已注定的悲剧,给了金大爷老两口沉重的打击。 几年后,金大爷病故,紧接着金婆婆也中风了。那时,金家老二已经定居外地,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;老三与家里关系不好,面对大哥一家如此大的负担,避之不及;唯一的女儿嫁得远,经济条件也很有限,有心无力。 这下,金婆婆的医药费、一家人吃的米面粮油以及日常生活开支,林林总总全压在了老金身上。亲友们觉得他可怜,去街道办为他争取了附近几条村道的保洁工作——老金活了40年,头一回有了正经工作。 老金一直弄不明白自己的年纪,脾气也暴躁,时不时大喊大叫,毫不顾及他人的目光。玲婶状态好一些,从外表看,她身上的衣着虽落伍,但收拾得挺干净,走路也规规矩矩的,碰见生人时必低下头,抬起眼斜斜地看,很温顺的样子。 每天早晨三四点钟,老金和玲婶骑着三轮车从家里出发,且行且停,一路清扫。到了下午,将挨家挨户收集来的垃圾运到几公里外的中转站,就算下班了。 我常听人说,智力落后人士对工作总是一丝不苟。可老金不那样,他爱犯懒,有时不愿出车,就让玲婶独自出门,自己躲在家里睡大觉。玲婶瘦瘦小小,哪里搞得定几条街的垃圾清运,一天下来总会留几处“盲点”,弄得街坊们很有意见。 老金外出干活的时候,只要碰见哪一户人家多倒了垃圾,或是把垃圾箱弄得乱糟糟,便骂骂咧咧。要是有人当着他的面乱丢垃圾,他直眼瞪过去,将大扫帚举过头顶,怒气冲冲,似乎马上就要冲上去动手……这样一来,邻里关系就越来越紧张。 前些年我去老宅办事,遇见老金推着金婆婆出来透风。也就只在这种时候,老金才会像个正常的儿子。他对母亲细言慢语,安分得像块石头。金婆婆瘦了很多,她的眼睛直勾勾的,眉头皱得像一把刀,布满皱纹的脸颊发灰,见到熟人也不招呼,像是心里存了莫大的仇怨。 后来,我与老街坊蔡老师说起这事儿,蔡老师叹了口气:“金婆婆时日无多,等她过身之后,谁来照看老金一家呢?” 再见小金,是在金婆婆的葬礼上。 那天阴雨绵绵,按照本地的丧葬风俗,逝者被安置于灵车之中,旁边的道士敲着锣,嘴里念念有词,既叙述逝者的生平,也夸赞后辈的孝意。金家儿孙披麻戴孝,围着灵车不停转圈,停步后开始游街。在扶灵队伍中,全是智力落后人士的老金一家格外显眼。 作为长子,老金身居首位,穿一件杏色麻质孝衣,头包白毛巾,一只手攥着一支缠了白布的“哭杖”,另一只手搭在灵车的边沿上。他红着眼,不住地流泪,悲伤到了极点。小金跟在后头,也是同样的打扮,但神情大不相同——他苦着脸,表情恍惚,走一会儿就停下来挠挠脸,动动脖子,在后头叔伯们的催促下,才紧赶慢赶跟上队伍。 算起来,我和小金已经有七八年没见了。我八九岁时,我们两家住对门,小伙伴们一同出去玩,小金就在后头转悠,畏畏缩缩地想同去,可金婆婆怕小金受欺侮,总拦着。小金也很顺从,不哭闹,只是不说话。到了上学的年纪,小金读书读得很艰难,小学未毕业便辍了学。他在家里瞎晃了几年,就由亲戚带到外地去做工,想让他长点见识,也许能学得聪明些——如今的小金已经长得跟他父亲一样高瘦了,他像年轻时的王志文,只是目光迟钝,少了一份书卷气。 智力落后程度是分轻重的。小金症状在家里是最轻微的,他生活完全能自理,与亲戚交谈也通顺,只是在待人接物和工作方面比正常人要欠缺一些。有时家里来个人,门口过个街坊,小金只用目光稍一打量便回过头,要么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要么就躲进小阁楼,从早到晚见不到人影。 金婆婆下葬后,大家从墓地回来,主人家照例要招待亲友饮食。租来的桌椅瓢盆摆在金家的院子里,厨师们吆喝着传菜,搬运酒水,一派忙碌景象。 老金缩在角落里发呆,对身旁来去的人群浑然不觉。他与母亲的关系最深厚,以他仅有的智商,想必也意识到了这场白事的涵义。而小金早早上了席,大嚼肉食,对家里的哀事置若罔闻。 不知为何,我看到这一幕,心底忽然十分悲怮。 3 老金刚辞去村里的清扫工作时,有人说是因为老金“懒性发作”,嫌这活儿太累;也有人说是因为村里改制,清洁工作被街道办打包给了第三方公司,老金夫妻不愿接受规范化管理,还闹出了不少冲突。 总之,老金失业了。他闲在家里,时不时要和玲婶吵一架,有时他抓着扫帚扫自家院子,身子扭来扭去,像在地上写大字,一笔一划,一折腾就是一下午。玲婶就坐在家门口,呆呆地看着。 这样的光景,邻居三婆都看不下去了,她介绍性格温和的玲婶到附近的服装厂做事。工厂是本村人开的,了解老金家的难处,特地安排玲婶“剪料”——革面上已经用粉笔画好了线,只要用剪刀划开就是,上手难度很低。一天只要她做6小时,开3000块的工资。 可惜没过多久,玲婶便被辞退了。三婆找工厂管理层打听情况,对方说玲婶大约是第一次进工厂,对什么都好奇,剪料剪到一半就去看车间里正在运作的压花机。压花机上的辊筒周而复始地碾来碾去,密集的齿轮组一会儿松开,一会儿又紧紧地咬合,确实有些朦胧的工业美,但其中的危险哪里是玲婶可以理解的?车间主任怕出事,就投诉到了东家那里。 玲婶只能继续做家庭主妇,她去菜市场买菜,总往虾皮摊子跑,咸腌小螃蟹几块钱能买一大堆,再买几个又扁又圆的芜菁,来来去去就这么几样。鱼贩子阿生是个善心人,他的鱼档生意不错,偶尔有缺头少尾的鲜鱼卖不上价,就一并拢在袋子里,朝玲婶招招手,一股脑儿全塞在她的菜篮子里,只象征性地收几个硬币。 玲婶有时还不领情,嘟嘟囔囔:“这鱼我不会烧,我不想要。” 玲婶的母亲大概只教过她蒸鱼:细皮嫩肉的黄梅鱼往锅里一架,水煮干了挖半勺调味素,就能下筷子了。碰到一些皮糙肉厚的海鱼,玲婶就毫无办法,她既不会控制火候,更不晓得切姜丝,只好洗一洗丢进锅里煮汤,鱼肉都煮散成糜,腥味弥漫。 到了夏天,老金照例在院子里摆一张扑克桌,边乘凉边喝萝卜稀饭。浙江台每年都要重播的86版《西游记》,算是老金夫妻少数可以理解的电视节目之一,虽然听不懂台词,但他们仍对孙猴子变的戏法拍手叫好。 饮食、衣着、《西游记》,这是老金父母教给他们的一切,他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,没有改变也无法做出改变。这个由三个智力落后者组成的家庭,他们的生活永远停滞在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。 4 小深将拆违通告贴到文明巷的时候,谁也没当回事。 这些年,时不时冒出些小道消息,今天说文明巷要整体打包拆改啦,明天说要清理违章建筑啦,但雷声大雨点小,最后总是不了了之。这次风风火火的“百日攻坚”,大家觉得也一样。 可是没过多久,金家的院子就率先“热闹”了起来。 老金夫妇还在干保洁的时候,在院子里搭了一个车棚,停放了两辆改装三轮车。剩余部分被捡来的塑料瓶、麻布袋、废旧金属和零零碎碎的杂家什占据着,它们垒在一起,堆得跟小山似的。 老金家后院的矮墙外,是一个本村人开的塑料小作坊,生产汽配零件,比如卡车上的门把手、油箱盖、尿素盖之类的小玩意儿。这几年消防查得严,要求这家小作坊把生产用的易燃材料独立储存。可是小作坊连车间都不够用,作坊主便想到了老金院子里的车棚——那儿正对着作坊后门,正好安置大桶大桶的胶水。 作坊主和老金的兄弟商议后,将八九平米的车棚改建成仓库,每年的租金有千把块。这个数目虽不多,但已经让老金很欢喜了。 然而,正是因为这个棚子的存在,让年近古稀的老金狠狠地跌了个跟头。村委会领了拆改任务,先联系老金的弟妹,又通过街坊们递话,想让老金“自拆自改”,给出的期限是3天。后门的作坊主也配合,听到风声,早早退租,将整间棚子腾空,还多付了老金几百元租金。 可是,无论村干部、街坊、弟妹们怎么劝说,老金仍固守己见,含糊不清地重复嘟囔:“我的。”“我的房子。”“这是我的房子。” 世上唯一能说服老金的人是金婆婆,可她已经过身6年了。 3天后的清晨,保安公司的中巴开到文明巷头,老金仍在院子里扫地,丝毫没有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文明巷里人潮涌动,上百人围观这次“拆违”行动,眼看工程车推掉巷头的一间平房后,就直接转向了老金家的院子,一路轰鸣而去。 人们开始朝那儿聚拢,妇女们挤到警戒线外,头碰头地低声议论。得到街道办负责人的示意后,几个保安径直走向老金,他们配合默契,每人困住一条肢体,以抬猪的姿势将老金捞了起来。 老金吓呆了,只会“啊啊”地叫,无论他如何哀嚎,保安们都面无表情,他们穿过人群,将老金一路抬到村委会,那里已经安排了几位街坊,负责安抚老金的情绪。小金呢?他依旧躲在小阁楼里,从始至终都没有露面。 1小时后,玲婶将吓得哆哆嗦嗦的老金搀回家,昔日满满当当的院子里已经空无一物,只留下满地的残石碎瓦了。老金失去了他的简易棚,有很多真正的垃圾可扫了。 以老金的智商,他也许永远弄不明白这件事的缘由。什么是“一类房”,什么是“三类房”,什么是“街道办”?他更不会理解——为什么对门邻居的简易棚不用拆,偏要拆他家的? 5 再见小深是两个月后。他辞掉了街道办的工作,转投市区交警队做文职,工作轻松了许多,薪水也翻了番。 “早知道交警队福利这么好,鬼才想干街道。”小深一脸哀怨。 他说让自己下定决心离职的因素有很多,“老金也是其中之一”。“拆违”结束那几天,他下村核对文件,发现老金时不时尾随他,阴嗖嗖的目光看得他脊背发凉。小深撇撇嘴道:“老金可一点都不傻,我搬出去10多年了,他不仅认识我,还记得我的名字。因为那个棚子的事,甚至记恨上我了。” 这几年,小深在街道办做的工作又多又杂。上头要查违章建筑,他就开着“综治办”的电瓶车到处转悠,摸底做汇报;市里的安监部门下来查消防,他大多要跟在后头,也亲手剪过不少小作坊的供电线。 我挤兑他:“拉的仇恨太多,是该挪一挪屁股了。” 小深脸色铁青,沉默下去。 提起老金,我问小深:莫说全市,就以新塘街道来说,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有一条“文明巷”呢?搁平日里,连本村居民也很少走这条破落的小道,“你们怎么下得去手?跟一个傻子较什么劲?” 小深摇摇头,将前缘后果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 这两年的“拆违”工作与前几年大不相同。前几年,市里推行的“拆违”计划侧重闹市区和商圈,像文明巷这样的边缘地带,不过做一做动员工作而已。基层人情关系复杂,市里的布局像是一阵风,来得快去得也快,风平浪静后,“拆违”往往不了了之。如今,市里动了真章,开始使用卫星数据作比对,将疑似违章的照片下发到镇和街道,再用无人机实地考察确认。一旦辖区里的违章建筑被拍成照片,形势就陡然紧张起来,街道就像领了军令状,没有半点人情可讲。 “用卫星和无人机拍违章?”我瞪大了眼睛。 小深点点头,言语中有颇多无奈:“那可不,街道也买了好几架无人机,还找了家第三方技术公司专门培训了两个‘飞手’,每隔几周飞手们就要四处出击,做一轮详细的重点巡查。” 我忽然觉得很荒谬——老金一家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,头顶的天空之中,电子眼正在窥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 无人机在文明巷的上空停留,飞手会看到什么呢?当然可以看到那些丑陋的简易棚。除此之外,大概还能看到老金的院子里的那张扑克桌,桌上那碗煮成糊糊的鱼汤、白水煮的芜菁,以及三双茫然的眼睛。 想到这里,我有些义愤填膺:“这不是区别对待吗?” 前几年我搬去市中心的小区住,顶楼业主私自封了天井改成阳光房,我投诉到城建部门,对方回复倒挺快,说那些阳光房是“既成历史问题,需要慢慢研究解决”。然而,在百度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文明巷,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简易棚,街道办却迅速推掉了。 小深摇摇头,意味深长地说:“你不懂,在文明巷这样的地方,道德通常都与法律有所冲突。这种事没有对与错,只有各自的目标和考量。” 6 今年清明刚过,又有几户老街坊从文明巷搬了出去。曾经吵闹的小巷,如今静谧极了,时代抛弃了它,只留下一个空落落的外壳。 我家老宅早已不住人了,成了放杂物的仓库,为了将有限的空间利用起来,我定做了几个存储架,准备搬进去。可是,要将宽大的仓储架搬进狭长的老宅谈何容易,不一会儿,文明巷就被堵了个严实。 这时候,老金骑着三轮车从巷口过来,我一面催促搬运师傅加快速度,一面赶紧跟老金打招呼。 听邻居说,老金最近找到个新差事,替一家胶垫厂做手工。这活儿不难,从厂里拉来的胶皮是半成品,中间留着一块压好的密封垫,只要用剪刀剪去外围废料再修整修整,就算是完成了一件。每天早晨,老金从胶垫厂拉一箩筐半成品回家,傍晚再送回去。这活儿是计件的,多劳多得,他们夫妻一个月干下来也有两三千元的收入。 老金的三轮车后面拉着一车胶皮,要往家里运,我挡了他的道,心里有点慌——几年前,我到老宅清点库存,停在巷子里的车就挡了老金的道。当时他大声嚷嚷,胡乱骂一气,我也只能忍受着。我想,老金的世界终究与我们不同,在他的认知里,可能没有“忍让”的概念。 但奇怪的是,这次老金没有骂人,还默默地站到我的身后。“那个,那个,拉开一点点就可以……”老金拍拍我的肩膀,又用手指比划,嘴唇上下翻动很快,我听了两遍才从他含糊的嗓音里明白了他的意思。 我点点头,移开路旁的仓储架,顺便给老金搭了把手,将分量十足的胶皮篓子从三轮车上搬下来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一直在仔细端详老金的面容。 他今年该69岁了,脸颊与眼角出现了零星的老年斑。寻常人到了这个年纪,经历了大半生风吹雨打,总会淬炼出一双睿智的眼睛,像是看透了这个世界。在我从前的印象里,智力落后的人大多都有一种孩童般的稚气,眼神里很难看到半点饱经风霜的沧桑感。以前的老金就是这样的,出了门便东张西望,对什么都很新鲜。可如今的老金,脸上的神色竟是我从未见过的深沉,他嘴唇紧抿,眉头微微皱起,像是在思考什么难题。 他将胶皮篓子搬到家门口,吩咐玲婶干活,又回到我的身侧。他背着手,不说话,看两位搬运师傅喊号子,将仓储架一点点往里挪。我问起那个被拆掉的车棚:“村里有没有给你一点钱补偿?” 老金摇摇头,将袖子挽起来给我看,手臂上有一块乌紫的淤青。“被打了,很痛。”老金平淡地说,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,像是说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小事。 回家后,我对母亲说起老金的变化,母亲一时怔住了。她20岁嫁过来,亲眼看着老金从小伙子熬成一个老头。她闷闷地想了一会儿,片刻后才说:“老金啊,也是会长大的啊。” 老金长大是被迫的。他的父亲死了,母亲也死了,唯一对他友善的二弟一家也远在外省。我想,老金能察觉到这些变化。普通人想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可以从书本上学习知识,可以从旁人身上借鉴经验,但智力落后的人只能依靠自身与社会规则的碰撞,依靠吃一堑长一智的血泪经验,才能渐渐悟出生存技巧。 失去了庇护的老金只能丢掉没有用的好奇心,磨去暴躁的脾性,学会温驯与服从、妥协与沉默。他花去60余年终于长大了,可惜他在这个世界走过的路已经很长,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 7 文明巷的街坊们大多已经搬离,但新家住的都不算远,仍然互通有无。没有人知道,小金是如何与玲婶沟通自己想要讨老婆的意愿的。 得知消息,退休前当过妇女主任的三婆立即发动身边的交际圈为小金物色对象,并很快有了目标。那个女孩姓林,30来岁,已经嫁过两次了。她智力落后程度不算太重,娘家条件也不错,给了一套房子做嫁妆。不过,这个女孩的卫生习惯不太好,又喜欢到处乱跑,总是不过半年就被夫家送回娘家。林家长辈心灰意冷,就将择婿标准一直放低。 谈起林家,三婆的眼睛都放出了光:“女孩上头有兄弟,已经成了家,父母手里有不少存款,还有好几套房子,小金这事要是成了,保管能过上好日子。” 我听了心里有些压抑:“嫁过来当然是好事。不过万一有了孩子,问题可就大了。假若小金的孩子也是智力落后,那该怎么办?一家子都没个正常人,谁来照顾婴儿呢?” 从小到大,我听过不少关于金家父子的“逸事”——据说,老金年轻时曾偷偷带小金去菜市场看热闹,仅百来米的路,转头就把儿子忘在了人群里。要不是金婆婆发了疯似地寻找,小金早就被弄丢了。 小金的智商状况当然要比父亲好一些,可如今“鸡娃”横行,家长们拼了命也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成长环境,就算金家第三代是个智力正常的人,小金又能给他的孩子留下什么呢? “说不定——”三婆顿了顿,有些底气不足,“能像明明的孩子一样聪明呢?” 明明也是住文明巷附近的智力落后人士,他同老金一样娶妻,生下一个女儿。这个女儿自小就很聪明,大学毕业后进了电商公司,30来岁就当上了经理。如今,明明一家已在杭州定居,住市区的大房子,女儿请了专职保姆照料父亲,明明的晚年生活非常安逸。 “就像摸奖一样,碰碰运气。”三婆轻声说。 我摇摇头:“这个摸奖的成本太高了。” “谁不知道让两个傻子生孩子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?可你说的是高高在上的理论,我说的则是现实问题。”三婆又将问题抛给我,“老金夫妻俩去世之后,小金该如何自处呢?” 我喉咙动了动,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,因为这的确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。老金的兄弟姐妹不少,多少还能帮衬一些,可小金是独生子,与上一辈叔伯感情疏远,更不要说同辈的表兄与堂兄了。等老金夫妇故去,谁帮小金打理财产、处理这些社会事务呢?如果他娶了林家女孩,林家多少能照顾到小金。 世界上最残忍的事,莫过于将这些只有八九岁智商的“孩子”推向复杂的社会。更残忍的是,不得不继续做下去。三婆望着老金家的小楼,忽然没来由地说:“要是老金当初不娶亲,事情就好办多了。” 金家老二这些年在外省做生意,听说效益不错。老二媳妇对老金也关心,过冬换季时总会带一些衣服鞋子回来,时不时还要给老金寄一些零食。如果老金跟随他们生活,该是最好的选择,可现如今老金成了家,老二反而难以插手。家家都有难处,老二就是再有钱,也没有精力去照料一个智力落后的三口之家。 过了几天,林家那边传来消息,这事儿吹了。据说,林家长辈经过多方打听,意外了解到老金和玲婶都是智力落后人士,于是几位牵线的大妈被狠狠地骂了一通。 三婆愁眉苦脸,只顾叹气:“倒不能怪林家的长辈,他们也是为女儿的将来考虑。” 智力落后人士相亲也是有鄙视链的。但凡有一方是普通人,不管家庭多困难,长相脾气多差,那也是第一等受欢迎。智力落后人士的父母心里明白,若是没有普通人照料,自己死后,孩子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的几率实在渺茫得很。就拿老金来说,能像他一样活到快70岁的智力落后人士非常少,走丢、被拐、因无法沟通病情死亡,乃至莫名其妙的意外事故,都会让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能够安安稳稳地老死,十无一二。 如果实在没有普通人可以选择,若是父母健在且有社保,也算是相当不错的条件。再下一等,有一位智商健全的兄弟姐妹,也是可以接受的。 如此看来,老金无疑是幸运的。他的父亲精明能干,给他留下两间遮风避雨的砖瓦房,更有一位任劳任怨的母亲为他娶妻带孩子。在那个年代,同龄人的生活条件不见得比老金更优越,所以除了那个被强拆的简易棚,他不完美的人生仍算是简单、平顺的。 小金的境遇则复杂得多。他是独生子,家庭条件也不太好,父母又都是智力落后者。这些几乎给他的婚事判了“死刑”,没有人会愿意将女儿嫁给他。 离开金家那方小小的院子,整个新塘街道、整条文明巷都像一只快速滚动的车轮,“轰隆隆”地不断向前,高速的发展让一些普通人都难以适应:我们用着电子身份证,在互联网上分享各自的人生;我们在社交APP上谈论健身、谈论30万公里之外的“嫦娥五号”;我们喝着大洋彼岸的咖啡,神经被比特币的疯涨牵动…… 老金和玲婶的时代行将谢幕,小金的路还很长。可他困在那间砖瓦房的二层阁楼里,踏不出半步。也许,他将孤独地走完这一程。 (文中人物名、地名均为化名) 编辑:罗诗如 题图:《海洋天堂》剧照 投稿给“大国小民”栏目,可致信:thelivings@vip.163.com,稿件一经刊用,将根据文章质量,提供单篇不少于3000元的稿酬。其它合作、建议、故事线索,欢迎于微信后台(或邮件)联系我们。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(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、事件经过、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)的真实性,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:人间theLivings(ID:thelivings),只为真的好故事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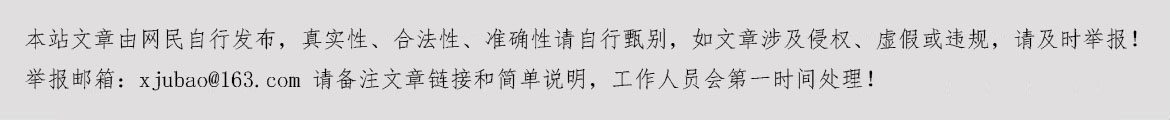
|
 鲜花 |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• 新闻资讯
• 活动频道
更多




